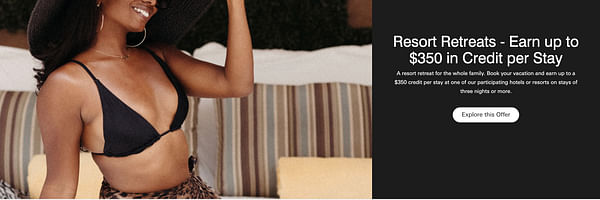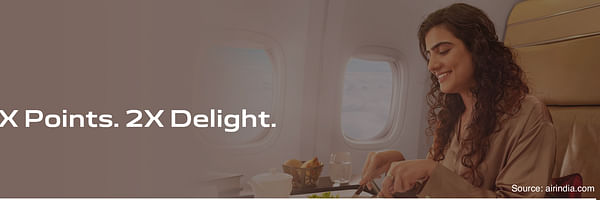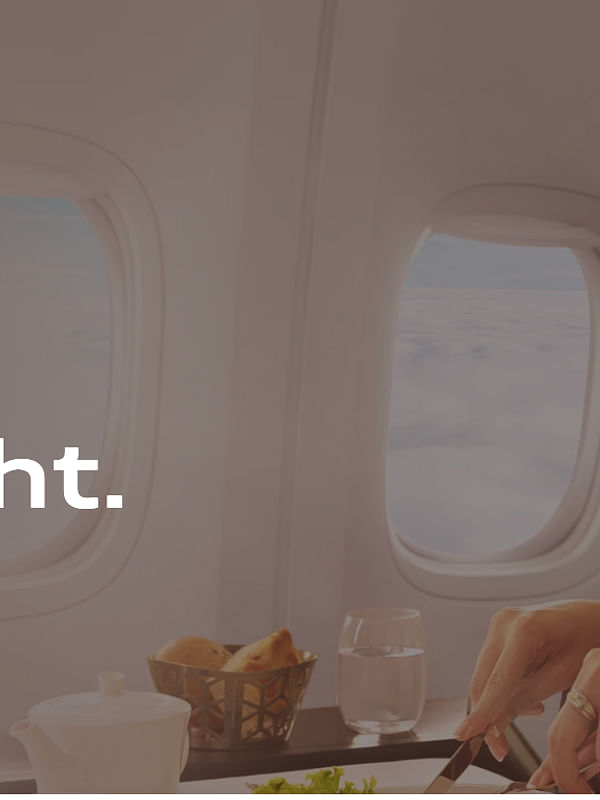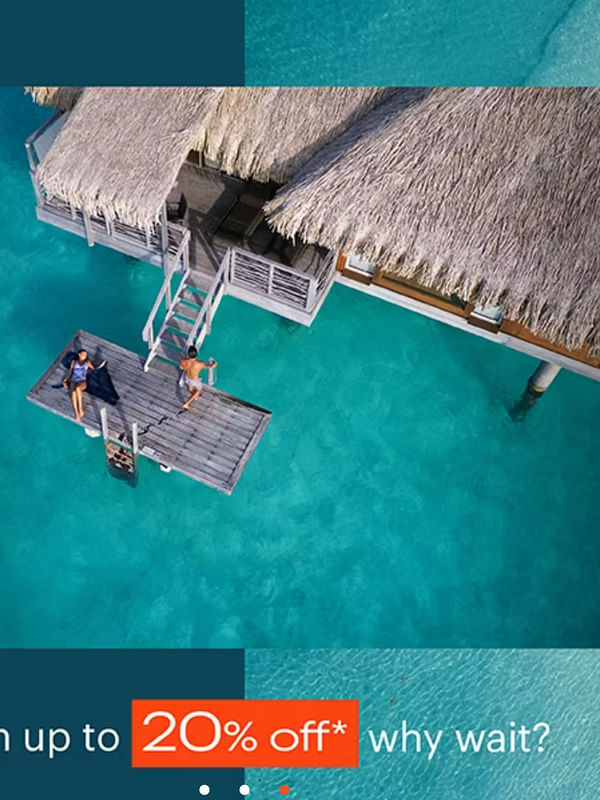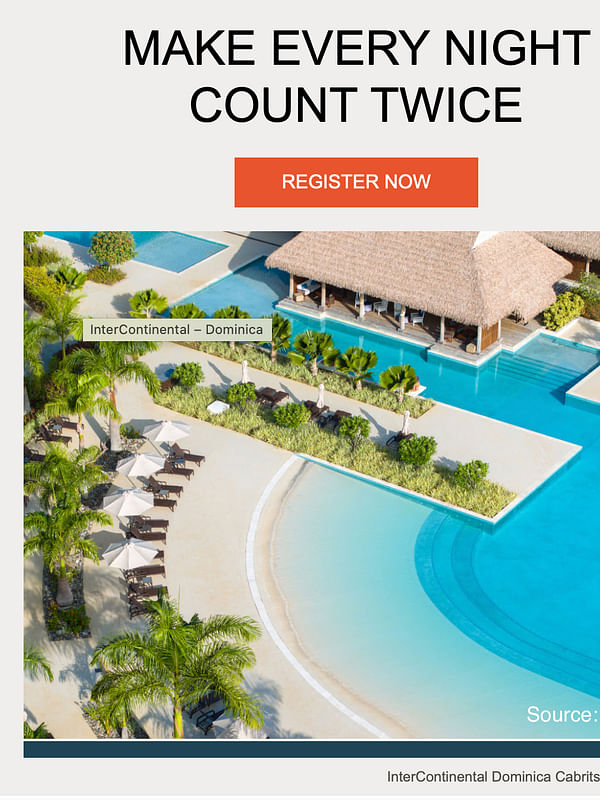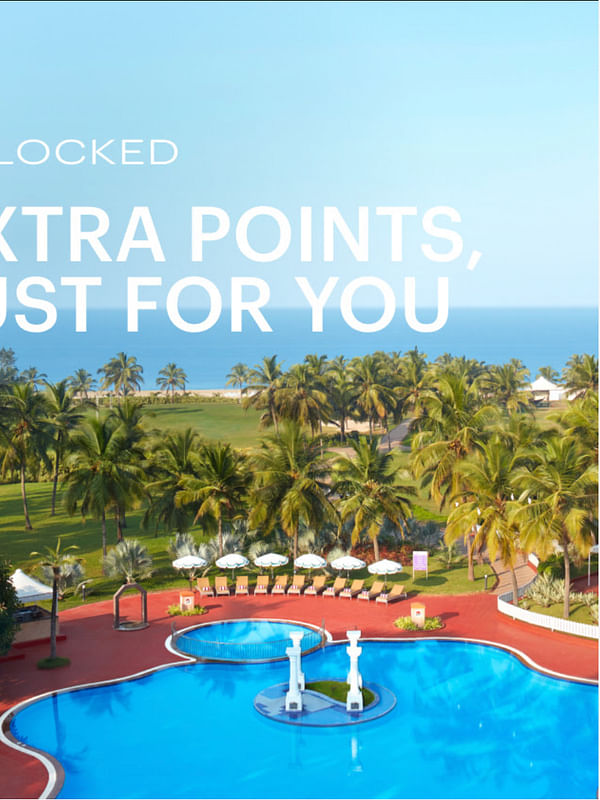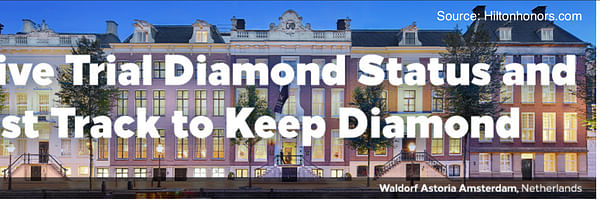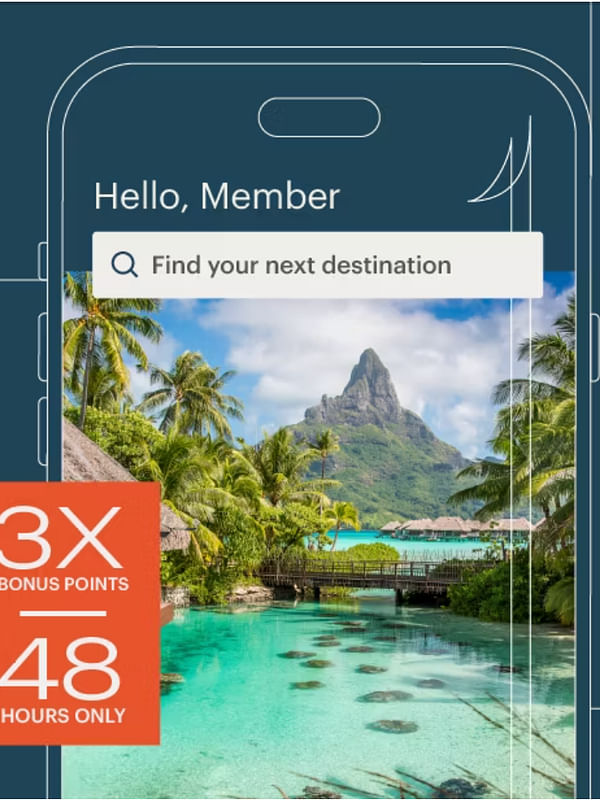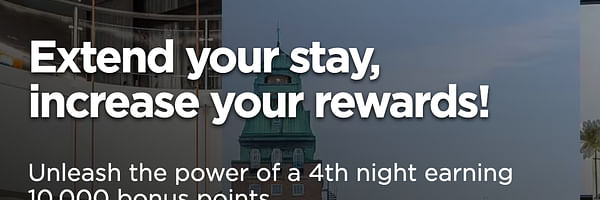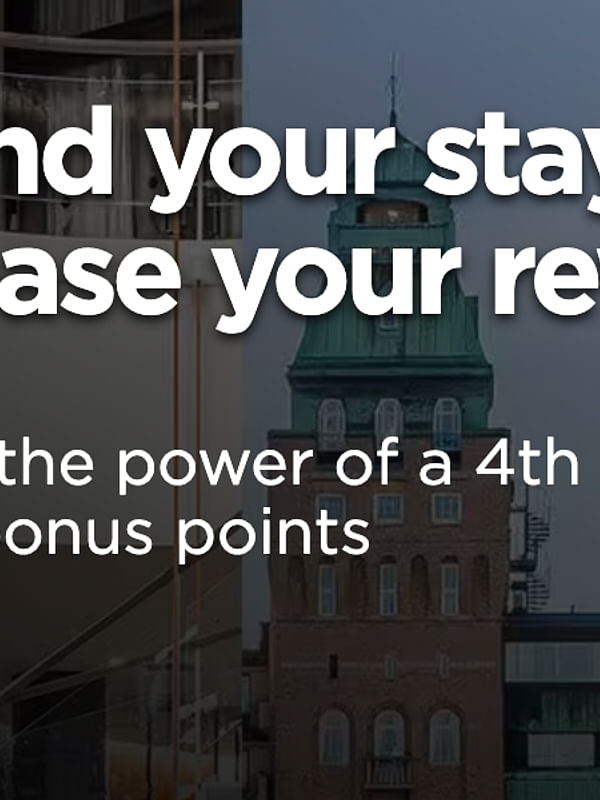Accor ALL
Reminder to register your credit card for Accor Dining Rewards.
All you need to do is register your credit or debit card with Accor. Once registered, you can earn Accor ALL points every time you use that card to pay at participating Accor restaurants.